- 相关推荐
浅论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
摘 要:形象思维,作为一切艺术表达的共同特征和共同方法,对于再现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小说和诗歌的角度,分析了形象思维是如何在翻译中展现原作的神韵和美感,避免呆板和僵硬的译作的。通过观察和分析,成功的译作,都是在利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特色,使译作充满生机,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关键词:文学翻译;形象思维;小说;诗歌;艺术
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学大师都在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国的李泽厚,都把形象思维当作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 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1 形象思维的概念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始终依赖于具体的形象和联想、想象来进行思维的方式。众所周知,形象思维是由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此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许多西方美学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典藉中也有着大量的同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论述。
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于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定义形象思维的,“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而说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与精义在于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不管是哪个定义都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它是文学工作者进行创作时必须调动的思维模式。
2 形象思维与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论中虽未出现“形象思维”的字眼,但是有关它的论述却自成体系中国文学创作者很早就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与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有关,单个汉字(早期的甲骨文最具代表性)便是脑海中的一个形象,甚至十几个形象组成的画面。其中以早期甲骨文最为典型,因为那是汉字的最初原始形式,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尤其是上实际的汉字改革-变繁为简。很多汉字已经失去象形特征。但也有不少保留,比如休息的“休”字让人联想到一人靠在树上歇息的画面。这种造字的思维模式运用于文学创作上便是形象思维。
中国古代有关形象思维的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论,象即为形象。子曰:‘立象以尽意’,正始时期,王弼以庄解易,融二家之说而进一步发挥。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一象尽,象以言着。这一段可简化为“言”→“象”→“意”的认识链条,即通过言象以达意。在这个认识链条中,“意”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然而,“象”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言”,只是“明象” ;而“象”,才能“出意”;无“象”,即不能达“意”。可见形象思维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固有特征。
文学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文学创作是意-象-言的过程,那么文学翻译便是言(源语)—象—意—象—言(译入语)的过程。即译者运用形象思维,调动一切感官活动,透过语言符号文本,通过想象和联想把物化的形象转化为译者心中的审美形象,再用另一种语言符号将其物化,其物化过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维。用形象思维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语文本,再运用形象思维去表达原作,建构目的语文本,形象思维贯穿于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
二 形象思维与文学翻译
1 形象思维对文学翻译大有裨益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翻译一定程度上可杜绝误译、死译、硬译。兹举例说明
原文:A rude noise broke on these fine ripplings and whisperings,at once so far away ans so clear:a positive tramp,tramp;a metallic clatter, which effaced the soft wave-vanderings;as,in a picture,the soild mass of a crag,or the rough boles of a great oak,drawn in dark and strong on the foreground,efface the aeiral distance of azure hill,sunny horizon and blended clouds,where tint melts into tint.
译文1:一阵如然而来的猛烈声音,那样辽远而又那样清楚,打破了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这确是阵阵踏地声,是金属的得得声,它将轻微的浪声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张图画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树的粗干,又黑又粗画在前面,把那有着碧蓝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线,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远方,给抹煞了一样。
译文2:一种粗重的声音,遥远而清晰,打破了这委婉的汩汩声和低语般的喃喃声,一种确确实实的脚步声,一种刺耳的得得声,把轻柔的水波流动声盖住了,犹如在一张画中,大块的岩石,或者大橡树的粗硬树干,用暗色画出来,在前景显得十分强烈,把青翠的山峦、明丽的天际和色彩互相渗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组成的茫茫远景压倒了一样。
本文摘自《简爱》,简爱第一次见罗切斯特的经历,选自第十二章,这里有许多动作描写和对人物外貌了解。“rude noise”分别被译成“突如而来的猛烈声音”和“粗重的声音”,这两种译法均未能很好的表达出rude一词的意思。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简当时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风景和悦耳的流水声被这声音破坏了,所以这个词仍宜译为“一阵粗暴的声音”。此段最后,blended clouds,where tint melts into tint,两种译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译为:“色彩交融的云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翻译过程中丢弃形象思维,那么译者下笔就枯索呆滞,语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动活泼,如同枯木一般毫无声息,与读者便觉译文艰涩生硬,惨不忍睹,原文风味尽失,意境全无。这样的译本应该是钱钟书先生所指的“消灭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运用形象思维,才能使译文生动,符合译入语的文章习惯。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七缀集》第69页)
文学翻译中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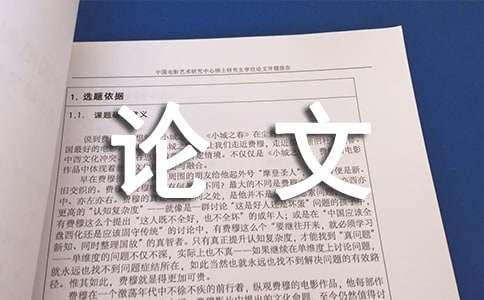
【浅论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相关文章:
浅论文学形象的叙事翻译和语用翻译03-18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的论文12-01
浅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的学生自主学习03-18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1-27
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形象思维训练03-20
形象思维在英语学习中的运用论文11-26
浅论非言语行为意义的翻译03-18
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与文学作品教学论文05-10
试论文学翻译中汉语模糊美的磨蚀与补偿03-17